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小說家夏目漱石堪稱是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學巨匠和代表性的國民作家,他的作品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其創作出一系列長篇傑作,細緻地揭示出日本近代社會中的變貌、日本人幽微的心理狀態,及其關於生活方面的細節。而正是這個文學性的描述特質,一多百年來,其作品持續受到廣泛閱讀和研究。更準確地說,他的小說具有跨越時間的現代性,直通人性和生活的底蘊,給研究者開闢了詮釋的空間,並得以回顧和見證明治時代的光明與黑暗。從這個意義來看,這無疑是讀者們的幸運,因為他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見他藉由小說人物道出人生中的不幸源頭,這不但需要勇氣和智慧,更需要高超的寫作技藝。也許,我們甚至可以說,比小說寫作技藝更重要的是,作家挖掘人性靈魂的本領,唯有做到這種高度的人才是卓越的小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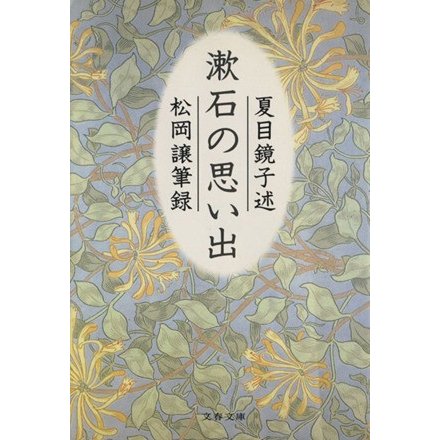
作家的履歷
夏目漱石(1867-1916)本名金之助,正如其父親命名時所冀望的那樣,希望這孩子將來可以得到金援和衣食無缺,然而,命運之神卻不這樣安排,漱石反而有個坎坷波折的童年,這似乎是上天要他成為作家之前必要的磨練。漱石的父親原本是舊幕府時期世襲的「名主」(職司街道行政警察),但明治維新以後,整個家境就敗落了。因此,他 2 歲的時候,被送給他人做養子,直到 9 歲才回到父母身邊一同生活,只不過,這幼年寄人籬下的生活,造成了他孤僻的性格。所幸,後來他接觸漢學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心靈的荒蕪才獲得了滋潤。1879 年左右,他由東京府第一中學轉學到漢學私塾二松學堂。1883 年,為了學習英語到進入「成立學舍」,這時他已開始展露出文學才華。1888 年,他升入第一高等中學本科,與俳人正岡子規同年級,兩人交往甚深。那時候,正岡正規製作輯入漢詩和俳句的手抄本《七草集》文集,給同學們相互傳閱,他則在卷末寫上評語,他們因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誼。1890 年,漱石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進大學後不久,由於他學習成績優異,很快就獲得文部省免學費優等生的待遇。1893 年大學畢業後,擔任東京高師的英語教師。兩年後,突然辭職,先後去了四國松山市松山中學和九州熊本市第五高等學校任教。1896 年 6 月,漱石與貴族院書記長中根重一的長女鏡子結婚(參見夏目鏡子《漱石の思い出》一書)。1900 年,他以文部省官費留學生的身份到英國學習英語教學,而非英國文學研究。在英國,他汲取了諸多西方的文藝思潮,觀察到在「文明開化」的西方社會中存在著各種弊端,同時他更深切體會在歐洲中心主義之下,亞洲人遭受的人種歧視。弔詭的是,這些刻骨銘心的經歷,很大程度地改變了他的文學創作觀。在他看來,與其一輩子無趣乏味地教授英文,不如創作小說來拯救自己受縛的靈魂。三年學業期滿回國後,他在東京帝大執教,於此期間,在文學知交高濱虛子主編的《杜鵑》雜誌上,撰稿和發表俳句。1905 年 1 月,漱石發表首部長篇小說《我是貓》的第一章,旋即獲得好評,正是這部筆觸幽默諷刺和批判明治時代醜陋的社會現象的力作,讓漱石一躍登上了明治文壇。在文壇立足以後,漱石又陸續寫了許多作品,其中包括幾部中、長篇小說。例如《少爺》(1906)、《虞美人草》(1097)等。對於漱石而言,1907 年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轉折,因為《朝日新聞》邀請他為報社特聘作家,他便辭去東京帝大教授之職,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在這以後,他又創作了七、八部長篇小說,如中期作品愛情三部曲《三四郎》(1908)、《從此以後》(1909)、《門》(1910)和晚年寫作《春分之後》(1912)、《行人》(1912-1913)、《心》(1914)、《路邊草》(1915)、以及生前未完成的《明暗》長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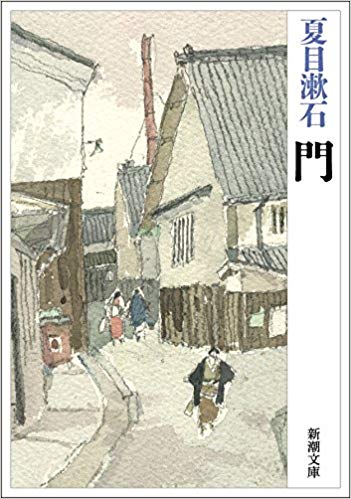
門內故事的開端
小說《門》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描寫主軸在於野中宗助和妻子阿米二人平凡幸福又隱藏不安的家庭生活,由於他們的經濟狀況不佳,向某個幕府晚期官員後代的姓坂井的房東租屋,與其他房客共用一個女傭,但是彼此恩愛相互扶持,對未來的生活倒沒什麼不滿。儘管後來宗助遇到叔父臨死前典賣亡父託付的房地家產,留下一筆難算的爛賬,嬸母又向他表明,她已經無力為寄居家裡的小六(宗助胞弟)繳納學費,今後小六必須搬去與宗助同住,這等同於把生活重擔移到宗助的肩上。不過,宗助對這些困難都正面迎接下來,小六也沒有淪為無用的米蟲,積極地到工廠做工,為自己開啟了新的生活。照理說,他們倆應該無所遺憾,但偏巧有兩件大事,一直橫亙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事實上,妻子阿米原本是他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時期的同學安井的同居女友。不過,安井卻向宗助佯稱,阿米是他的妹妹。因同學的緣故,宗助經常到安井的住處走動,便與阿米多了些互動,日子一久,阿米對宗助產生了情愫。而宗助沒念完大學,就與阿米結婚搬到廣島和福岡了。兩年後,經京都帝大的同窗友人杉原的介紹,宗助在東京謀得了一份差事,他和阿米從此賃居在東京僻地的山崖下。其二,就是阿米的無可慰藉的遺憾。因為阿米好不容易三度懷孕,但最後卻都流產和死胎,讓她覺得很對不住宗助,阿米認為,沒有子女的家庭,終究是破碎和不幸。而不幸對於精神的壓迫是沒有期限。當他們倆打算在這簡陋的住處安享餘年之時,有一次,坂井房東卻向他們說,其弟弟有個到滿洲闖蕩姓安井的朋友即將來訪,這個消息卻讓宗助夫婦大為震驚和尷尬,因為他們背叛朋友的良心譴責又席捲而來。即使後來宗助推測,依照安井的身體狀況和性格來看,他應該不會到滿洲或(殖民地)台灣那些地方去的。可是,這終究是宗助的個人臆斷,在這一刻來臨之前,他們倆頂多只是內傷外癒而已,根本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甚至還煩惱是否要搬離現在的住處,到其他地方重新過日子?
生活中的政治事件
從時間順序來看,夏目漱石發表長篇小說《門》的時點,似乎帶有某種設定歷史事件的巧合。這部作品於 1910(明治 43)年 3 月 1 日,開始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翌年 1 月,由春陽堂出版。該小說故事的開篇設定時間為 1909 年 10月31日星期日,乍看去,這是極其平常的日子。但就在開啟此故事的五、六日前,時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在哈爾濱火車站遭到埋伏的安重根槍殺身亡。畢竟,漱石是深知小說的寫作之道,即使他關注或反對當局的政治人物,甚至想直言批判,也不宜赤裸裸地和盤托出,而是藉由主角宗助兄弟倆和妻子阿米的對話,船過水無痕似地顯現出來。例如在第三章中,他這樣寫道:
宗助從妻子的手中接過飯碗,沒說一句話,就開始吃了起來,而小六(宗助的胞弟)也拿起了筷子。這三個人就這樣無拘無束地暢談著吃完了這頓飯。
「想不到,伊藤(博文)先生也遭到了厄運!」最後,小六換了一種口氣說。其實,五、六天以前,宗助看見報導伊藤公被暗殺的《號外》時,來到廚房對著正在做飯的阿米說:「喂,不得了,伊藤先生被殺啦!」他把《號外》放在阿米的圍裙上,又回到書齋了。聽他說話的語氣,倒也很平靜。「你說不得了,但從口氣中卻聽不出你有什麼震驚。」阿米特地半開玩笑地提醒他說。從那以後,每天的報紙上總有五、六段關於伊藤公的事。不知宗助是否看過這些報導,他對於這起暗殺事件似乎無動於衷。自從那天發表《號外》,直到今晚小六又一次提起這件事,夫妻倆對那些震驚天下的新聞,並沒有激起過特別大的興趣。儘管如此,接下來的對話才是重點所在。「他是為什被殺的?」阿米又向小六問了一遍。「有人用手槍砰砰連發幾槍,就打中了。」小六據實以告。「我是問你,他為什麼被殺呀!」小六起先不知如何回答,稍後口氣沉靜地說:「可能是命中注定吧。」阿米不明白他的語意,進而問道:「他為什麼又到滿洲去了呢?」這時,小六一本正經地說:「聽說要到俄國去幹一樁祕密的事情。「是嗎?他可真倒霉,遭人殺啦。」阿米說道。這時候,宗助才有聲有色地說,「像我這樣的小職員,被人殺了是倒霉的,但是像伊藤先生這種人,去哈爾濱被殺,倒是件好事呢。」小六追問道為什麼?「為什麼?伊藤先生一旦被殺,他就成了歷史的偉人。要是無聲無息地死去,就不會這樣。」小六似乎認同哥哥的看法,過了一會兒,接著說:「不論是滿洲還是哈爾濱,都是容易動亂出問題的地方,我總覺得那裡很危險。」
工筆與微物
如果我們把視點從政治事件稍做挪移,聚焦在夏目漱石對於宗助夫妻倆租屋處的話,尤其對於周遭環境的描寫,將會驚訝於漱石的寫實主義功力,絕不遜色於任何一位工筆畫家,甚至在表現上更勝一籌。以第二章為例,他這樣描寫家居的風景:「經『魚勝』酒館的門前,走過五、六戶人家,從一個既不靠馬路,也不接連巷子的地方拐過去,頂頭就是一座高崖,左右兩邊排列著四、五間格局相同的出租房屋。直到不久前,在那道稀疏的杉樹牆垣後面,還住著一個武士。房屋古樸而閒靜,與普通人物夾雜在一起。誰知崖上邊有個姓坂井的人,還下這塊地皮,拆除了茅草房頂,拔掉了杉牆,重新改建成現在這個樣子。宗助的房子正對著巷子,位於最裡面的左側,而且緊貼著崖下,顯得陰森森的。」在此,必須指出,這段描繪不禁使人想起了巴爾扎克的小說《高老頭》開篇處的寓所景致。緊接著,漱石又寫道:「宗助坐在昏暗的客廳裡,默默地在小火爐上烤手取暖。木炭在裡面燒的通紅。這時候,他聽到崖上房東家的小姐在彈鋼琴。宗助若有所思站起來,拉開客廳的擋雨窗,走到廊緣上。斑竹在灰暗的天空裡抖動著枝條,一兩點星光閃閃爍爍,鋼琴聲不停地從斑竹的後面傳過來。」在第七章中,「他向下一看,寒森森的竹子寂然不動地鎖在早晨的霧氣裡。朝陽映照著竹梢,溶化了枝葉上的寒霜。崖下二尺左右的陡坡上,枯草奇怪地剝落下來,露出新鮮的紅土層。宗助有些驚訝。他們這裡順著坡面一直向下看,發現自己站立的廊緣下的泥土地上的白霜被踩過了。宗助以為這可能是一條大狗從山崖上掉下來造成的,然而轉念又想,狗再大,也不會踐踏得這樣厲害。/由於日照不足,再加上雨水老是順著竹筒流下來,每逢夏天,這裡就長滿了秋海棠。到了旺季,綠葉簇簇,蔥翠茂密,連道路都堵住了。這些秋海棠在杉樹牆垣拆除之前,就常年日久在地上滋長著。今天,古老的房子坍塌了,每逢時令一到,它照樣長出嫩芽來。」讀到這樣的文字,所有具體的影像和聲音都如此順利地映入我們的眼簾了。另外,他在描述宗助治療牙痛的情景,同樣寫得維妙維肖,彷彿我們就身歷現場一樣:「不知怎的,一不小心磕著了,門牙頓時感到鑽心地疼痛。用指頭一扳,齒根搖搖晃晃的。吃飯時喝熱茶就疼,張口呼吸又怵冷風。這一天,宗助早晨刷牙,特地避開痛處。他用牙籤剔牙時,用鏡子照了照口腔,發現他在廣島鑲銀的兩顆臼齒和磨損得高低不平的門齒閃著寒光。/牙醫師在宗助的牙根部開了一個小洞,插進像針一般細長的東西,然後拔出尖端聞了聞。隨後抽出一根絲狀物給宗助看,告訴他這就是牙神經,已經取出來了。接著,他把藥填進小洞裡,叮嚀宗助明日再來複診。」

消逝的面影
除了景物的深描以外,夏目漱石對於他筆下人物的明治時期的物價都有詳細記載,而不是瑣碎的流水賬。歷史性地考察,這樣描寫似乎成為應然的寫作傳統,滲入了日本作家的血液裡。譬如,漱石的同時代作家永井荷風(1879-1959)即是如此,他在六卷本《斷腸亭日乘》中,對於日常生活的物價記載,無意間為研究者提供了解當時物價變化的參考資料。從這意義上而言,漱石的寫實筆觸無疑也在挽救那些已經消逝的面影,一同把明治時代的各種聲音,統統鎸刻在他的文字天地裡。進言之,漱石是個性情中人。他在現實生活中,其家庭婚姻生活是美好的,完全不像宗助夫婦倆的苦悶與徬徨。在最後一章中,他為宗助道出了心聲:「宗助眺望著前方,前方鐵門緊閉,永遠遮擋著他的視線。他不是一個能走進這門的人,也不是一個不進門可以安心的人。總而言之,他是一個佇立門下等待日落的不幸之人。」事實上,漱石對於這對夫妻更完美的描述是:他們在相互契合之中找到了普通夫婦難以得到的親密和滿足,同時也伴隨一種倦怠感。他們的內心被這種抑鬱的倦怠佔據了,然而,他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幸福的。在這世人眼裡,這對夫婦依然是普通的夫婦。但在他們彼此看來,兩個人已經成了道義上不可分離的有機體。而構成這對夫婦精神境界的每一根纖維都是雙方相互絞合而成的。他們簡直像掉落在大水盤的兩滴油,將水彈起以後便自然地匯聚在一處了。順著這個邏輯反思,正如愛情有其自身的辯證法一樣,當它被逼向窮途末路之時,不幸往往就是幸運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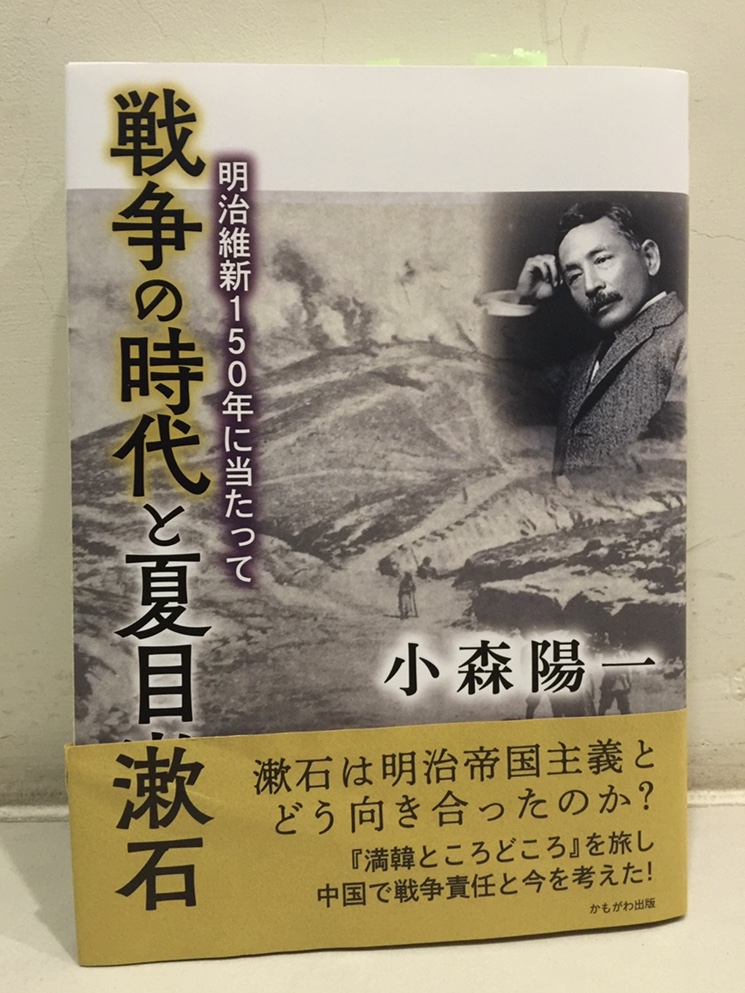

評論被關閉。